
列文森的老师费正清是“挑战—回应”型汉学研究模式的开创者。在这种研究视角下,中国近代所发生的各类变化都变成了回应西方冲击的结果,而中国内部生发出来的历史动力则在不同程度上被忽略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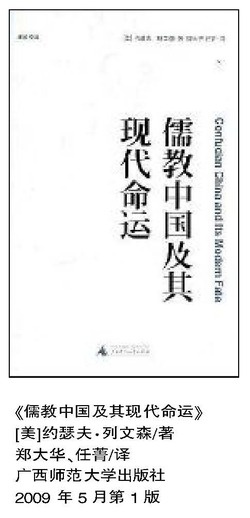 对思想的历史根基的强调并不是说,即使没有西方的冲击,近代中国也会在原有的根基之上发展出各种近代化的思想形态;而是说,对西方之冲击的过分重视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将导致对思想史层次性考察的欠缺。
对思想的历史根基的强调并不是说,即使没有西方的冲击,近代中国也会在原有的根基之上发展出各种近代化的思想形态;而是说,对西方之冲击的过分重视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将导致对思想史层次性考察的欠缺。
作为费正清的高足,列文森在西方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正是列文森的代表作。在此书中与其说列文森在展示中国近代思想的原貌,还不如说他在分析思想构造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心态。正因为此,虽然列文森并未大段大段地引用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原著,也未细致地考证各种言辞的本来含义,但思想的跃动却获得了更为实在的展现。
首先,他考察了自明末清初至西方入侵前的中国思想界的一般状态。显然,在这段历史中,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被誉为“乾嘉学术”的考据学。考据学的目标是探讨文献的真实状态,它排斥虚幻的哲学论说,因此体现出一定的科学精神,这一点被列文森风趣地概括为“挖洞是向下挖,神是神圣的人,人是人类,世界具有世界性”。然而,这种风趣的论断实际上暗藏着列文森对考据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评价。在列文森看来,考据学很少系统地提出问题,也切断了自己迈向科学的路径。既然科学思维推动了西方的近代化,而考据学与科学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那么考据学只能属于传统。中国文人的非职业化心态扩张到治学领域所产生的结果是,士大夫所学之物充满了空洞的内容且基本无助于治国实践。至此,列文森切实地为清代思想盖上了“传统”的印章。
封闭的文化圈使传统思想博得了足够的自尊。然而,当西方打开了中国文化圈的缺口并使传统士大夫认识到在中国文化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可选择的同样发达的文化时,士大夫就被抛在了诸种选择面前。尽管选择的出现是强力介入的产物,但最先遭遇西方文化的中国士大夫显然不愿承认中国文化的残败。那么,他们究竟如何面对挑战呢?
列文森认为,处于西方冲击中的近代中国思想界开始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迎接挑战:其一为发轫于曾国藩并由张之洞集其大成的中西调和论;其二则是倭仁所提倡的排斥西学论。在列文森看来,曾国藩和张之洞的主张意欲在维护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同时,为引入西方的技术提供理论准备。“它通过赋予这种僵死的物质以‘活’的性质,从而消除了那种受人恩惠的感觉。”但事实上,中西调和论或者说作为其完成形态的“中体西用论”都是失败的。而倭仁的排斥西学论明显只是在无用且无力地抗拒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可以说,曾国藩、张之洞和倭仁出于维护中国文化之主体地位的焦虑心态而设计的学说最终都成了被否定的思想选择,而中国近代的思想进程则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今、古文经学的角逐。
作为清末今文经学的代表者,康有为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接受西方的理论基础。不过,在列文森看来,康有为所欲构建的绝不是纯粹西方化的话语体系,而是有助于传统儒学吸纳西学的经典背景。他认为,真正的儒家精神一直被扭曲着,所以改革不仅应获得允许,而且也是重新发现“中国”的本真和名誉的过程。与今文经学者一样,作为古文经学者的章炳麟也认为真正的传统从未落后于西方,因此有必要对传统作出重新认识。然而,学说体系的自相矛盾宣告了古文经学者幻想的破灭,而今古文学者的共同失败则意味着试图以儒学来包容西学并将二者铸为一体的构思也成为了没有希望的思想选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章炳麟都试图寻找“真正的儒家精神”来重树传统的权威,而他们的失败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儒家精神”的失败,因此传统就完全暴露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并走到了无处可退的地步。于是,民族主义者开始了自己挽救传统的历程。
在列文森的观念中,民族主义者的亮相是与中国人的天下观被国家观代替的过程同步进行的。“天下”一词与其说代表着一种地理范围,毋宁说是一种文化概念。它所坚守的价值为,与列国相比,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因此,秉持天下观的同义语就是维护传统的文明形态。与“天下”不同,“国家”是一个实体概念,它所强调的是建基于国力之上的独立地位。所以,对实体的存续来说,遵守固定规则就是迂腐的代名词。在与列强的较量中反复失败的事实使天下观已成为幻影,现实的问题是,在恢复“天下”秩序无望的情况下如何为中国争得“国家”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化中,民族主义诞生了。列文森列举了民族主义者的两种举措:“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和批判基督教。然而最终列文森又否定了民族主义者的思想选择。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展示了列文森对近代中国几类思想选择的阐述。众所周知,列文森的老师费正清是“挑战—回应”型汉学研究模式的开创者。在这种研究视角下,中国近代所发生的各类变化都变成了回应西方冲击的结果,而中国内部生发出来的历史动力则在不同程度上被忽略了。列文森显然继承了费正清的研究模式。然而,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真的是无根的吗?如果我们“赤手空拳地进入历史”,就必定会摇头否定。比如,在考察康有为的公羊学时,我们可以一直将思维延伸至清代中期以庄存与、刘逢禄等为代表的常州今文学派。又比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研究朱子学及阳明心学时就已经指出,明清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公”的色彩,而这种色彩也影响到了中国近代人物的思想构成。对思想的历史根基的强调并不是说,即使没有西方的冲击,近代中国也会在原有的根基之上发展出各种近代化的思想形态;而是说,对西方之冲击的过分重视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将导致对思想史层次性考察的欠缺。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定列文森对近代中国之思想的解读。他颇具哲思而又充满“生存意识”的论述体现了他对思想史的独特理解。在他的笔下,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中西文明之间的沟通所激发出来的文化现象的整合。《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之所以充满魅力,其原因就在于它展现了近代思想所暗藏的文化心态、列文森对诸种思想的自我体认以及从其体认中引发出来的忧郁感;它之所以受到批评,其原因也正在于它的过于思想化和历史感的稍显不足以至于让人感到一种玄之又玄的模糊感。不过,这也许就是列文森的独特思想风格,也是列文森之所以成为列文森的理由。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
邮政编码:100026
事业发展中心(广告发行) Tel:010-85885198 Fax:010-85885198 E-mail:fxb_zzs@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