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学通:加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中国是经过殖民解放运动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一个民族独立国家的。因此,中国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和殖民地国家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在相当程度上是模仿西方国家的。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内生的,它的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传统文化以及整个政治哲学思想是其民族国家的内生基础。而中国没有这个基础,中国是从外面借鉴来的,但又不能全盘效仿西方。
在我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既借鉴了外部思想和模式,又与中国特有的基础相结合,这也是我们的方法和必然路径。在这个必然路径中,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在西方语境中,“国家”的概念和“民族”的概念是一致的,所以叫民族国家。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美国不叫民族,他们叫种族,尽管各种族不同,但是都属于美利坚民族。而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非民族国家。当年,孙中山先生提出用“国族”一词来代替“民族”。到现在我们还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原因是观念没有转变。
中国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是正确的,就要采取一切有利于培养所有公民的“中国人”民族认同的政策。凡是不利于或破坏个人形成“中国人”民族认同的政策,都要进行修改。
中国采取了很多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措施,但西方部分媒体仍在鼓吹中国毁灭少数民族文化。其实,西方很多国家根本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也没有鼓励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政策,都是采取统一语言教学的政策。因此,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方面,我们不要顾忌西方说什么。要明确一个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讲,是让全体公民有共同的民族认同重要,还是让别人表扬几句重要。
应该肯定地说,和之前相比,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状况还是有了很大提高。当清政府派第一批留学生去日本读书时,这些人在填国籍时居然填出四个国籍:清人、汉人、华人和中国人,可见当时中国人对自己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认识是多么混乱。
但是,在成绩面前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正视问题。我们在民族建构问题上缺乏一个明确的方针,我们政策中的矛盾使得民族一体化进程严重受阻,民族分裂主义的事件不断发生。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国际社会产生了一个观念,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者国际社会认为一个分裂的中国是合理的。可以说,能不能完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关键一环。(本报记者 范勇鹏 李彩艳 采访整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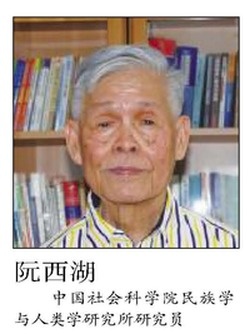 阮西湖:拉美经验 ——强化国籍概念
阮西湖:拉美经验 ——强化国籍概念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地区之一,据2005年的统计报告显示,拉美总人口为5.6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17%。但是其民族成分异常复杂。从各个国家情况讲,由于民族构成不一,各国民族理论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也不尽相同。加强对拉美民族及其民族理论的研究是摆在世界民族学家、都市人类学家、拉美历史学家以及政治学家面前的经常性课题。根据我在加勒比地区了解情况和收集到的资料,得出拉美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几种模式。
巴西民族是一个混合民族,包括白人、黑人、穆拉托人、梅斯蒂索人、桑博人。据我了解,“巴西人”是国籍称谓,不是民族概念。巴西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地域辽阔、各地差异很大的国家,它推行的是“种族和文化熔炉政策”。
我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期间,遇到一位巴西黑人。他说,在巴西,黑人不受歧视,但他认为应该建立黑人文化。巴西的民族关系是和睦的。巴西在1888年取消奴隶制,一百多年来,黑人与白人能够和睦相处,不受歧视。这一点引起国际上的注意。这可能与巴西重视“巴西人”称谓有关,都是“巴西人”,大家都一样。
同时,一体化政策与同化政策不同。在人类学上,一体化有专门的含义,即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吸引,但彼此主要特点依然保留,这种政策主要在墨西哥推行。但目前在墨西哥对一体化政策存在不同意见。
民族发展论是近期拉美地区提出的新的民族理论。这一理论与一体化政策是对立的,其主要观点是主张印第安人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他们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实行自我管理。这一理论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很值得重视。
另外,国籍称谓理论突出国家属性,同时又承认存在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这种国籍称谓对唤起爱国主义热情和国民中的团结友好相处很有好处。在世界杯足球赛中,每次巴西队的出场都牵动全体巴西人(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心。可见,国籍称谓能增强各民族的爱国热情,阿根廷人也是如此。
随着全球化的继续深化,多元文化将长期存在,多民族也将与其同在。因此国籍称谓的意义也就越来越重要了,这有利于民族和谐相处。不同居民在使用国籍称谓时,也不会有被同化之忧虑。当然,在使用国籍称谓时,我们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多民族国家里居民双重属性;国籍称谓包括所有民族的居民以及这些居民对国家所作的贡献;多元文化社会的长期性是国籍称谓存在的意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研究。(本报记者 褚国飞 潘启雯 采访整理) 瓦·季什科夫:民族因素在俄罗斯联邦的作用
瓦·季什科夫:民族因素在俄罗斯联邦的作用
20世纪末最后十年,俄罗斯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其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国家疆域的改变、市场改革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社会意识、人际关系、个人行为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的民族成分、文化多样性、族际关系的性质和有关“民族问题”的国家政策,即民族政策,也都受到了深刻影响。现在的俄罗斯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和社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尽管历史和传统,包括苏联时期的遗产,对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着巨大影响。
虽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人口具有民族多样性的特点,但它仍然和世界上许多大国一样,拥有不同民族出身和宗教信仰的人们。此时,重要的不是人口的文化多样性这个事实本身,而是社会和国家赋予人口的文化多样性这个因素什么意义。在这方面,俄罗斯的历史经验的确非常独特,其结果也不尽相同。
在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期,人们的民族差别具有特殊的意义,各民族同一体被称作“各民族”,而一部分国家制度就是按民族区域原则建立的。这有助于保留小文化和小语种。现在,俄罗斯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主要以非俄罗斯民族(少数民族)区域内部自治的形式存在,这些共和国和自治区是保留和发展小文化的经济、法律及政治的基础。现在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民族共同体理论和“多民族组成”形式。放弃公民国家的思想,不能把俄罗斯的联邦构成解释为实现俄罗斯的民族国家自治。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分析民族因素在俄罗斯的作用以及国家生活中发生的其他一些重要事情(人口、移民、冲突、极端民族主义、宽容及其他一些问题)。但对我本人和国家而言,其他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中国的经验,是极其重要的。中国支持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政策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中,民族区域自治形式的存在与中国的存在不矛盾,中国的存在不是由民族决定的,而是由全体公民民主决定的。占多数民族的汉族和汉文化的存在,不会排斥,更不会拒绝全中国人民对国家的一致忠诚。
对俄罗斯而言,这种模式具有重大意义,也许是拯救俄罗斯的良方。换言之,不应当以俄国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典型方法,而应当以确立俄罗斯统一和确立俄罗斯人为统一民族的思想和计划,对抗地方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当然,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汉族的民族主义一样,在两国的社会生活中都存在,但其内容可以并且应当向包容性、公开性和尊重文化复杂性的方向转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将来不会支持文化分立主义,而会支持文化多样性情况下的国家统一。实际上,俄罗斯不仅存在100多个不同民族,而且也存在一个统一的民族,这就是俄罗斯人国家和文化的一致性,但要使俄罗斯学术界和政治界意识到并承认这个现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中国、印度、墨西哥、西班牙和其他国家,存在着“多民族统一”的形式,在探索新的统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验将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益处。(高永久 翻译整理) 王希恩:民族融合 文化多元
王希恩:民族融合 文化多元
从全球来看,民族一体化、民族融合的趋势正在加快,可与此同时,民族冲突在局部地区仍比较严重。这其实并不矛盾。
所谓民族一体化、民族融合趋势加快,是说当今的全球化依据高技术在将地域空间急遽压缩的同时,也使人们在文化、观念上的共性前所未有地增多起来,民族的特殊性由此大幅度消解。但在这种共性增多的同时,人们对个性的追求、各个民族对自身利益和特殊性的追求也在增强,其中也包括追求“独立”和“分裂”企图的抬升。冷战结束以后,民族冲突不断成为世界局势的热点,各有其不同的具体原因,但主要根源在于与全球化有关的打破封闭过程中文化和各种利益的相互冲撞,而民族主义又在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理论指导”。
“民族主义”的核心精神,一是将“民族”神圣化,将民族这种自然的人类共同体提高到至高的、永恒的地位;二是主张“一族一国”,一个民族只有和一个国家对应起来才是合理的,人类才能幸福。历史上,民族主义曾在西欧造就了最早的民族国家,其后又掀动了波及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也仍然在以民族为单元的各类政治运动、思想学说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乃至支配作用。由于“民族神圣”实质上是在打造自己民族的神话,而在多民族国家中谋求“一族一国”,势必与相邻其他民族和多民族国家整体形成冲突。这是民族主义留给当今世界挥之不去的恶果。
我坚信民族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论点,也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人们不断为民族做出不同的定义,但都承认民族是人类历史一定阶段的产物。有生就有灭,万物皆然,民族也不能例外。民族融合是一个久远的未来,也是一个过程,它的渐进表现就是民族特性的减少和共性的增多。马克思主义将民族与阶级和国家一道,视为终将消亡并致力于消亡的事物,因为它们或是人类隔绝的产物,或制造了人类的隔绝。相对于阶级的消亡,民族的消亡可能更为长久,但在它发展的进程中,共同因素的增多则是社会的进步。民族以文化为本,但两者并不等同。文化可以是民族的,也可以是地域的、阶级的、家族的、年龄的、性别的,它们之间又是可以交叉重叠的。
所以,文化是人类的本质属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创造性的源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而民族则是会消亡的。民族的消亡或融合只意味着人类这种群体之间界限的消除,失去的只是人类交往的屏障,而不会是文化和文化的多样性。所以,民族融合、民族消亡是人类的进步,我们提倡文化的多样性,却不能提倡民族隔阂。这与国际上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是不矛盾的。
当今虽然远不是民族融合的时代,但我们决不可以抗拒民族之间的接近和共同因素的增多。固化民族之间的界限和强行推进民族融合一样,都是违背民族发展规律的。(本报记者 潘启雯 采访整理) 周勇:民族冲突的四个根源 ——种族主义、资源争夺、宗教、语言
周勇:民族冲突的四个根源 ——种族主义、资源争夺、宗教、语言
全世界所有国家中,绝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在一个多民族共处的国家,要维护稳定的民族关系,首先必须尊重文化多样性。这表现在生活方式、语言、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文化的多样性,对于国家的发展是一笔财富,而不是一种阻碍。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化多样性也是适应自然生态性的产物,例如在游牧民族聚居的草原地区,就不适合搞农耕和农田开发。为此,有一种现象值得特别警惕,这就是人类社会不能采取单一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使狩猎、游牧、农耕等传统生活方式边缘化,单线进化论不能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交往更加频繁,民族发展表现出了多种形态。与此同时,民族冲突在局部地区也愈发严重。在导致民族冲突的根源中,最严重的是种族灭绝。种族灭绝在二战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1948年联合国大会为此出台了《防止和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但是,不要以为种族灭绝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事实上一些国家或地区仍然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卢旺达、南斯拉夫等一些国家。我们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国家法律体制有时尚不足以有效防止乃至根除这一“罪中之罪”。这是值得特别警惕的。
对资源的控制和争夺,是导致民族冲突的重要根源。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往往资源比较丰富。由于资源过度开发,当地环境受到破坏,从而导致少数民族不能继续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于是,当地政府或者以跨国公司为背景的外国政府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如今,国际上很多土著民族纷纷掀起反抗商业开发项目的运动,就是最好的说明。不能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由,毁坏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及其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对宗教的不宽容,特别是国家政权的中立性和世俗性原则的违反,同样是导致民族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不说,这在日常生活中仍表现比较明显。例如,在欧洲生活的伊斯兰信徒就常常与主流社会发生冲突:穆斯林做礼拜是在周五,西方基督教做礼拜是在周日,因此一些在欧洲大学工作的穆斯林为此要求学校调课,校方没有接受,双方自然就会发生冲突。法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连续不断发生的有关穆斯林学生是否可以在学校佩戴头巾的争论,也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此外,语言的地位和使用、传承有时也会导致民族冲突。在多民族国家,语言带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在某种场合使用什么语言,往往涉及个人尊严和一个民族的认同与发展。例如,比利时讲瓦隆语和佛莱芒语两个群体之间的争执,曾差点导致这个国家分裂。(本报记者 冯建华 采访整理) И·Ю·扎里诺夫:民族学应以基础研究作为优先方向
И·Ю·扎里诺夫:民族学应以基础研究作为优先方向
民族群体,无论怎样它们都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的一部分,它们脱离自己的历史地域而存在,这种历史地域常被想象成国家的形式。它们在别国的“文化领域”获得新的民族面貌,这种新面貌的特点取决于时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该群体成员的认同表现出来的认同过程完全有可能取决于别国的指令和本身的自决,而作为某种社会文化性质的民族性可能开始具有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差异。被构建主义者扩大运用于所有民族共同体类型的论题,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它丝毫也不能把现代民族学学科所面临的理论问题弄清楚,不论它是独立的学科还是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组成部分。
在谈论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后民族范式时,民族学家们似乎不应该完全脱离与民族问题有着这种或那种联系的社会现象。不但如此,也无须重复,现在已变成时髦的“(狭义的)民族”和“(广义的)民族”这两个术语已经被不只是学术界的许多人习惯地用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让他们来操纵这两个术语所标明的、决定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道路的现象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罪的。遗憾的是,许多社会现象变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当然还有新闻业等近科学的投机家们钻营的对象。新闻业越来越追求现代社会中的“第四权力”的地位。建立在用历史的和同步的观点看待人类社会的真正科学思维基础之上的另外一种观点和价值体系,应该成为这一无耻和无知的危险扩张道路上的最后界线。而对各种科学理论和观念(其中包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民族性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那些理论及观念)的理智整合,可能是这方面的保证。
在社会科学包括民族学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无论怎样都是将这些研究用于实际目的的各种国家—意识形态目标的反映。在每一种现象中起源都是很重要的:西方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应用的动机,这种动机在把人类学研究用作重要的政治力量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俄罗斯的民族学和地理学不同,它以基础研究作为优先的方向。在苏联历史的某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民族学被普遍认为是有害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只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后,它才在俄罗斯的社会科学体系中获准“登记”,并把对外国民族(其中包括它们在世界许多国家中的离乡分散者)的民族学研究列入了自己的学术武库中。(高永久 翻译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
邮政编码:100026
事业发展中心(广告发行) Tel:010-85885198 Fax:010-85885198 E-mail:fxb_zzs@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