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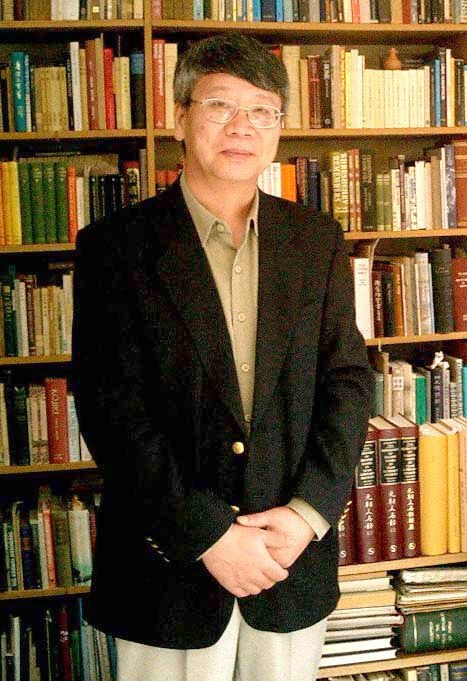
编者按: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7月27日在中国昆明开幕。这是我国首次申办的高规格、大规模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国际学术会议,被誉为“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奥林匹克大会”。本届大会由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承办,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联合协办,主会场设在云南大学。本次会议为期5天,来自近100个国家的300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册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界最具影响的世界性组织,其目标是加强社会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生物人类学等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其宗旨是通过集合不同领域的认识,以便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和促进自然与人类之间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该联合会每5年举办一次世界大会。本届大会主题“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Human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Diversity)直面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处境和问题,涵盖了人类学民族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全球人类无分古今中外都有着共同的自然禀赋、多样的发展需求和不可抑制的创新能力,这个世界因此才丰富多彩、充满活力。这一主题由中国方面提出,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同。
如果说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塔西佗古典民族志的渊源,且被誉为“人类学之父”,那么中国先秦时期“五方之民”的民族志记录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思想观念,无疑也可喻之为东方的“民族学之母”。
“中国田野”具有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资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不仅由于中国在亚洲大陆具有广阔的地理学版图,而且在于这一历史地理范围具有相当广泛的古人类遗迹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渊源。
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迹数以百计,旧石器时代遗址数以千计,新石器时代遗址则数以万计。中国是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资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浩繁的历史文献中,记录了大量文化多样性的群体及其互动关系。在汇集儒家学说先秦思想的《礼记》一书中,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夏”构成的“五方之民”的描述,开启了中国古典民族志的先河。这一记载指出:“五方之民”各有特性,他们的资质才艺,必然因其所处的气候和自然地理环境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性情、观念和行为方面,而且表现在语言、饮食、器物、工具、服饰、居所等方面。以中原文化之礼仪观念教化四方,须随其风俗习惯;以中原文化之政令法律统一四方,须因地制宜。
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观念中,不仅形成了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民族志认识,而且揭示了文化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进而产生了在礼教、政令、法律统一条件下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民族观。而这种观念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和而不同”观念在族际关系方面的集中体现。因此,如果说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塔西佗古典民族志的渊源,且被誉为“人类学之父”,那么中国先秦时期“五方之民”的民族志记录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思想观念,无疑也可喻之为东方的“民族学之母”。
修史纂志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重要的传统之一,也是中华文明不断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在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无论是中央王朝的官修历史,还是文人墨客的民间著述,无不包含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民族志方面的专门著作也应运而生。例如,清代官吏黄叔璥所著《番俗六考》,堪称第一部全面记录18世纪20年代台湾原住民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及其社会变迁的民族志。黄叔璥也因此被视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先驱”。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也记载了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志资料。如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其研究佛教史、交通史、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珍贵价值被翻译为英、法、德、日等文字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在这类记载中,有些记录是对一些古老社会及其文化形态最早的文字记录。例如,唐代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记载了地处贝加尔湖东北地区的驯鹿文化,精要地描述了该地区“畜鹿如牛马,使鹿牵车”,“人衣鹿皮,(鹿)食地苔,其俗聚木为屋”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特点。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环北极圈进行驯鹿民族调查时,这些记载提供的历史纵深感依然令人震撼。
同时,系统记录别国历史民族志的著作则属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1295年,周达观奉命出使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这部根据实地观察完成的著作,对当时的吴哥王朝及其社会、文化、习俗进行40个门类的民族志描述。这部著作的珍贵价值,在于它是记录13世纪吴哥王朝社会状貌的唯一著作。
公元1405—1433年,郑和率领明朝官方的庞大船队七度远航,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远抵东非海岸,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回了大量的世界信息,记录了大量的异域之民、他国之俗,是研究当时相关国家、相关民族的珍贵民族志资料。
在“中国田野”中,作为远古岩画传承的艺术,在中国古代建筑、洞窟、墓葬等遗址中发现的壁画和雕塑,以图像形式遗存的“五方之民”及其文化的资源也相当丰富。这些资料,为文化多样性群体的交流、融合、发展提供了历史证明,为拓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视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此外,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着以“类族辨物”为特点的分类传统。1903年,著名的法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发表了被誉为“社会学年鉴”学派最富启发性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即《原始分类》(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中国没有氏族的观念”。中国的分类传统是“星相”、“占卜”、“四季”、“节令”等。在这篇论文被译为英文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在导言中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认为涂氏的判断是“空口无凭的假定”。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族”(family)的概念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族”的分类从血缘、家庭、姓氏、亲属、地位、阶级、“夷夏”、邦交等诸多方面渗透于古代社会之中,成为划分人群的分类学概念。中国的“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们持续不断的互动,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它与古代西方源自古希腊文化的ethnos、nation具有同类意义。
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构成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本土背景和丰厚土壤。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事业的发展,伴随着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伴随着中国的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命运。因此,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也必然体现出中国学术传统中“经世致用”的治学特点。
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田野”中的早期实践
1793年7月,英国使臣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率领庞大的船队抵达中国,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建立贸易关系。然而,中英文化的礼仪之争和中国“康乾盛世”的优越自傲,使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的请求。对这一礼仪之争的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解读虽然视角不同,但是作为东西方之间一次重要的政治文化碰撞,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古老、传统的中国被纳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还是束缚于田亩的农民,这一历史变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从泱泱“天朝上国”的骄傲落入了丧权辱国的屈辱,从文化博大的优越落入了技不如人的自卑。这一切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并涌现了一大批救亡图存的先驱者。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的资料,为中国人打开了世界视野。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学”的概念和各种政治理论、学术思想开始大量传入中国。这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巨大的“西学东渐”。西方民族学知识的传入,为中国人认识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和国家统一性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种新的民族观念开始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nation)概念及其理论话语传到了中国。“民族”一词的广为使用,与中国在沉沦中崛起和寻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直接相关。
1905年,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面世。这是中国学人在西方民族学知识影响下撰著的第一部中国民族志。这部著作在反映中国“五方之民”互动历史脉络的同时,出于对国家危亡的深切忧虑提出“保同种”、“排异族”的振兴汉族之策。当时对这种民族主义话语的阐释,一方面出现了以塑造“黄帝”为标志的“黄汉民族”祖先崇拜,另一方面又迎合了所谓汉族源于西方的假说。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民族主义心态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吸收和应用西方民族学理论时,一方面解释着晚清中国的危局,另一方面构建着中国的民族(nation)。由此推动了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也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的传播创造了社会条件。
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之后,对中华民族的解读,成为中国社会由传统王朝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中的关键词。1911年爆发的中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统一性进程中,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族观念也经历了从狭隘民族主义,到成为代表中国各个民族总称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引起了学术界长期的争论,而且也推动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学者理解、阐释和应用本土的过程。在阐释民族学及其基本概念和理论的中国学人,莫过于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先生。1926年,他在《说民族学》一文中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他认为,通过民族学的视野,不仅能够对中国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远古文化现象作出科学的解读,而且能够使人们认识和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脉络,他特别强调了现代民族学的记录“就是事实要从考察上得来”的原则。这对中国学者形成重视田野工作的学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之际,正是中国第一所国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备之时。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设立的第一研究组即是民族学组,院长蔡元培兼任了组长。与此同时,在广州成立的中山大学,也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等方面展开了科研与教学的实践。这些学科性研究实体和教学科系,逐步聚集了中国第一代留学海外归来的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
193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出现了高潮。更加科学规范的学术引进形成规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形成了学习先进、应用本土、深入田野、创新发展的基本取向。1934年,中国学界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民族学会,《民族学研究集刊》也应运而生。一大批依托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包括台湾的原住民调查)的学术成果也相继刊布。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科学事业的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依托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历史学,所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始终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在1930年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迅速发展的时期,以中国民族史冠名的著作也纷纷出版,相关的论文大量刊发。其中,1936年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是第一部把人类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的著作。这些著作在解读中国“五方之民”互动的历史的同时,都对“中华民族”这一称谓和含义进行了探讨。
在有关“中华民族”概念的学术争论中,以历史学家顾颉刚和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进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战最具代表性。1939年,顾颉刚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从历史上民族同化和融合的视角,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从秦朝开始就逐步在血缘和文化上融为了一体的观点,他所论证的“中华民族”就是不断融入少数民族成分的汉族。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中,则从“民族”概念入手,分析了了中国人由不同文化、语言、体质的群体组成。总之,前者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单一性,后者强调了中国民族的多样性。围绕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历史学与民族学的对话,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几十年后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概括的历史背景。
学术界有关“中华民族”的争论,也引起了中国政治领域的重视。1939年12月,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新的解释:中国“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这一阐释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客观把握,由此也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民族—国家观。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事业的发展,伴随着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伴随着中国的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命运。因此,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也必然体现出中国学术传统中“经世致用”的治学特点。著名民族学、历史学家马长寿先生在倡导人类学应用于边疆政治研究时指出:“中国的人类学,固然不能放弃人类共同的一方面,但尤须注重中国人独有的一方面。”这种“独有的一方面”,也就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发展中形成了多学科结构的综合学术领域——民族研究。
1949年以后,民族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田野工作围绕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努力探索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立足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体现了“应该以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人的发展”这一观点。
当代“中国田野”的主题——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
1950年代,是中国经历了百年内忧外患后走上国家独立、人民自主、恢复经济、建设国家的时代。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来说,人类学、民族学在这个时期以非同寻常的形式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的“中国田野”。
早在1930年代,民族史学家江应墚先生就指出:“能对于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了认识,方能说得到了解我们自己,方能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在1956—1964年间,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展开的前所未有、规模巨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会、历史调查,这是对中国多民族国情进行认识的一次重大科学活动。参加这次田野工作的学者总数达到1400多人,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全国各个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研究,从数百个纷繁复杂的“自称”和“他称”中,进行了民族识别,为中国政府确认各个少数民族在政治、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提供了科学依据。确立了中国是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了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体。
中国的民族识别是国家主导下的科学实践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共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赋予少数民族根据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发展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的自主权利。这就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保护。
对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事业来说,这次旷日持久、规模巨大的田野调查,不仅为国家的少数民族事务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和重要的智力支持,而且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田野工作实践了为每一种语言写志、为每一个民族修史的学术目标,完成了数百部著作。当时拍摄的10多部民族志影片,开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声。这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完成的最好的学术成果,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学术财富。在大陆开展这项大规模田野工作的同时,1949—1965年间,台湾的人类学、民族学界也开展以原住民为主的田野工作。
如果说1950年代开始的上述调查研究,是为了赋予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那么1978年以来展开的田野,则是以各民族共同发展为主题的田野。发展,是当代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与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因此,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重视程度最高、投入力量最多的一个田野工作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落地生根最成功的西方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再度出现且更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使中国学术界的国际视野随之扩展。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理论、学派和方法,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国化”成为中国学术界努力探索的重大问题。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吸收先进的学术成就、发展中国的学术特色,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思考和实践。在这方面,外国学者和中国台湾、香港的学者,在中国大陆展开的田野工作及其刊布的学术成果,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田野工作围绕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努力探索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十分注重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中蕴含的传统智慧、地方知识和乡土文化,尤其关注文化认同、濒危语言、民间信仰、族际关系、自治权利、消除贫困、社会和谐等问题。这些研究取向及其宗旨,立足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立足于保护和传承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共同理念,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应该以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人的发展”这一观点。
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离不开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在多支点的发展中,国际化程度并不平衡。比较而言,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古人类学、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国际性影响显著,哲学社会科学范畴的人类学、民族学及其所关涉的诸多学术方向的国际化程度则参差不齐。在这方面,中国台湾、香港的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国际对话能力、交流合作能力具有优势。近些年来,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一些传统学科或专门学问,如民族历史学、蒙古学、藏学等,在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吸收借鉴方面日益增强。同时,中国学界对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少数人权利、原住民运动、公民社会、多元文化主义、国际移民等话题,也加强了研究。总体来看,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已经形成了开放、发展的态势,一系列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在进行,中国学人的海外民族志田野工作也初步展开。
中国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资源丰富的国度,同时仍然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欠发达的国度。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历史有过曲折,但是发展的现状则充满活力。中国是一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因素并存的国家。在这样一种长期的社会变迁中,社会制度的完善、社会问题的消解都处于一个动态过程。因此,中国的学术体制、学术规范、学术责任也将随着这一动态过程而趋于完善。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学术交流,可以加快这一过程。
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历来有应用性强的特点,这是“以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的题中之义。但是,应用性强并不意味着对理论提炼和方法更新的忽视。中国需要在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本土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方法。没有学科理论的发展,没有科学方法的创新,就不可能有效地实践应用。
(本版文章为作者所作大会报告,发表时略有删节)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
邮政编码:100026
事业发展中心(广告发行) Tel:010-85885198 Fax:010-85885198 E-mail:fxb_zzs@cass.org.cn